青洲山下的愛情故事─寫在《那時。花開》演出前
青洲山下的愛情故事
──寫在《那時。花開》演出前
婆仔屋藝術空間今年首次舉辦「牛房劇季」,跟過往在牛房倉庫藝術空間舉行的演出比較,劇季最特別之處就是這些委約性質的演出,大多跟牛房的空間特性或正於牛房舉行的展覽具較強的互動關係。
上月中的《一人一故事劇場:青洲坊拾壹街柒號》,以即興劇場結合本地年青錄像工作者何家政的紀錄短片,短片中,何家政訪問在青洲居住了廿七年的母親,觀眾觀賞完影片後分享自己的一些個人的青洲記憶,演出者即場以戲劇形式將這些記憶再現;正在舉行《好趁青洲留倩影》藝術展的牛房倉庫,頓時成了一個青洲記憶的倉庫,發言的觀眾雖然未必是青洲居民,但很多都是曾在該區念書或在青洲有過一些難忘經歷的人,當中有學生、在職人士和曾經到青洲進行創作的藝術工作者,這時劇場彷彿回復了她作為「社會論壇」的本質,劇場工作者在社區參與上的角色更見清晰。
劇場中的社區記憶
記憶,有時是感性的,一齣戲、一首歌、一張舊照,往往會勾起很多個人的童年往事、戀愛片段、旅行經驗......。不過,從近年諸多因社會發展而延伸出的種種公眾議題中看來,記憶,尤其集體記憶,當它跟城市的變遷進行角力的時候,原來是還可以有理性反思的空間。劇場工作者也許在生活的局限裡,未必可以藉由藝術呈現出真實的社區生活或社群的體驗,不過他們的表演技能及身體經驗卻可以幫助或引導民眾去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民眾對社區的關注與訴求。不過礙於時限,也可能是在引導故事上缺乏經驗,一個小時左右的分享與互動中,仍未有更深度的故事被引發出來,然而,「一人一故事劇場」作為一種有效的社區參與的劇場模式,是可以肯定的。
「一人一故事劇場」之後,同一個展場中將有另一個以青洲為題材的戲劇上演,由陳栢添編導的《那時。花開》將會透過一個愛情故事見證青洲當下,以及可以想像的改變。愛情故事,總是「老掉牙」的以離離合合為始終,單純的戀愛「循例地」在成長、在物質社會的影響下變質......。我問導演阿添為什麼要寫一個愛情故事?他說因為「青洲山」,這個因工程被砍去一大片,據說還已經被賣了的青洲山,真有如此浪漫嗎?阿添說他創作這個戲之前,特地到過青洲好幾次,他覺得青洲山給他的感覺是很「原始」的,看著這澳門僅存的一點綠,漸漸被破壞、變形,令他聯想到人本性的流失,就像一場無法「持續發展」的戀愛,多麼「老掉牙」卻又如此寫實。

無法持續的青洲之戀
說到青洲山的「原始」,他如何將這個戲放在牛房倉庫中上演?牛房又給他一個怎樣的印像?「乾」是他對牛房倉庫的第一印象,他說一邊創作,一邊想像著如何將這個戲放在牛房裡演出,牛房給他的「疏離感」直接影響著劇中人的語言,劇中三個人物,雖然是朋友,但即使面對面的說話,卻往往給人溝通不了的感覺,甚至是口不對心的;劇中每個人物都有一段獨白,而且要依賴唱歌去表達他們自己的感受。建築工地發出的嘈音,缺乏溝通能力的交談,從原始的青洲山,到真正「城市」起來的整個澳門,聲音多了響亮了,人與人的關係卻變得疏離。
三年前,我為澳門藝穗創作了《氹仔故事,她說》,戲中說了一個三代人在氹仔的真實故事,戲演完後不足半年,劇中提及的一位老人家離世,劇中出現過的氹仔場景如排角的涼亭、社工局飯堂、松樹尾舊消防局背後的那片空地,一個一個消失......;時間,總會走得比人快,尤其在今天的澳門。陳栢添編導的《那時。花開》,這個青洲廢車場前的愛情故事,戲未上演,青洲山就已經消失了大片翠綠,像童話愛情一樣聖潔的修道院更被改建成用途不明的「宿舍」。難怪阿添在故事簡介上如此寫道:「為甚麼當要失去時才懂得擁有?是平日過於無動於衷,還是太過心煩眼盲呢? 」
每個社區背後都有充滿戲劇性的故事,《那時。花開》裡一段在青洲山下「無法持續發展」的愛情故事,你要不要來見證一下?
──寫在《那時。花開》演出前
婆仔屋藝術空間今年首次舉辦「牛房劇季」,跟過往在牛房倉庫藝術空間舉行的演出比較,劇季最特別之處就是這些委約性質的演出,大多跟牛房的空間特性或正於牛房舉行的展覽具較強的互動關係。
上月中的《一人一故事劇場:青洲坊拾壹街柒號》,以即興劇場結合本地年青錄像工作者何家政的紀錄短片,短片中,何家政訪問在青洲居住了廿七年的母親,觀眾觀賞完影片後分享自己的一些個人的青洲記憶,演出者即場以戲劇形式將這些記憶再現;正在舉行《好趁青洲留倩影》藝術展的牛房倉庫,頓時成了一個青洲記憶的倉庫,發言的觀眾雖然未必是青洲居民,但很多都是曾在該區念書或在青洲有過一些難忘經歷的人,當中有學生、在職人士和曾經到青洲進行創作的藝術工作者,這時劇場彷彿回復了她作為「社會論壇」的本質,劇場工作者在社區參與上的角色更見清晰。

劇場中的社區記憶
記憶,有時是感性的,一齣戲、一首歌、一張舊照,往往會勾起很多個人的童年往事、戀愛片段、旅行經驗......。不過,從近年諸多因社會發展而延伸出的種種公眾議題中看來,記憶,尤其集體記憶,當它跟城市的變遷進行角力的時候,原來是還可以有理性反思的空間。劇場工作者也許在生活的局限裡,未必可以藉由藝術呈現出真實的社區生活或社群的體驗,不過他們的表演技能及身體經驗卻可以幫助或引導民眾去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民眾對社區的關注與訴求。不過礙於時限,也可能是在引導故事上缺乏經驗,一個小時左右的分享與互動中,仍未有更深度的故事被引發出來,然而,「一人一故事劇場」作為一種有效的社區參與的劇場模式,是可以肯定的。
「一人一故事劇場」之後,同一個展場中將有另一個以青洲為題材的戲劇上演,由陳栢添編導的《那時。花開》將會透過一個愛情故事見證青洲當下,以及可以想像的改變。愛情故事,總是「老掉牙」的以離離合合為始終,單純的戀愛「循例地」在成長、在物質社會的影響下變質......。我問導演阿添為什麼要寫一個愛情故事?他說因為「青洲山」,這個因工程被砍去一大片,據說還已經被賣了的青洲山,真有如此浪漫嗎?阿添說他創作這個戲之前,特地到過青洲好幾次,他覺得青洲山給他的感覺是很「原始」的,看著這澳門僅存的一點綠,漸漸被破壞、變形,令他聯想到人本性的流失,就像一場無法「持續發展」的戀愛,多麼「老掉牙」卻又如此寫實。

無法持續的青洲之戀
說到青洲山的「原始」,他如何將這個戲放在牛房倉庫中上演?牛房又給他一個怎樣的印像?「乾」是他對牛房倉庫的第一印象,他說一邊創作,一邊想像著如何將這個戲放在牛房裡演出,牛房給他的「疏離感」直接影響著劇中人的語言,劇中三個人物,雖然是朋友,但即使面對面的說話,卻往往給人溝通不了的感覺,甚至是口不對心的;劇中每個人物都有一段獨白,而且要依賴唱歌去表達他們自己的感受。建築工地發出的嘈音,缺乏溝通能力的交談,從原始的青洲山,到真正「城市」起來的整個澳門,聲音多了響亮了,人與人的關係卻變得疏離。
三年前,我為澳門藝穗創作了《氹仔故事,她說》,戲中說了一個三代人在氹仔的真實故事,戲演完後不足半年,劇中提及的一位老人家離世,劇中出現過的氹仔場景如排角的涼亭、社工局飯堂、松樹尾舊消防局背後的那片空地,一個一個消失......;時間,總會走得比人快,尤其在今天的澳門。陳栢添編導的《那時。花開》,這個青洲廢車場前的愛情故事,戲未上演,青洲山就已經消失了大片翠綠,像童話愛情一樣聖潔的修道院更被改建成用途不明的「宿舍」。難怪阿添在故事簡介上如此寫道:「為甚麼當要失去時才懂得擁有?是平日過於無動於衷,還是太過心煩眼盲呢? 」
每個社區背後都有充滿戲劇性的故事,《那時。花開》裡一段在青洲山下「無法持續發展」的愛情故事,你要不要來見證一下?
莫兆忠 (原刊於澳門日報.文化/演藝)
「牛房劇季07」之《那時。花開》
演出日期:6月17及18日
演出時間:晚上8時
演出地點:牛房倉庫
「牛房劇季07」之《那時。花開》
演出日期:6月17及18日
演出時間:晚上8時
演出地點:牛房倉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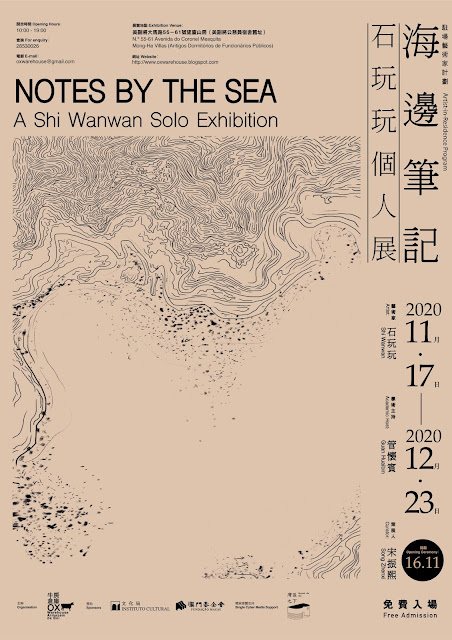

留言